2023年7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共七章62条,规定了适用范围、管理人和托管人义务、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内容。《条例》备受行业瞩目,其出台酝酿已久,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基金法》”)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监管;2014年,形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草案)》;2017年8月,国务院发布征求意见稿,并连续多年被列入国务院立法公章计划;2023年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草案)》;本次公布后,《条例》将于2023年9月1日正式实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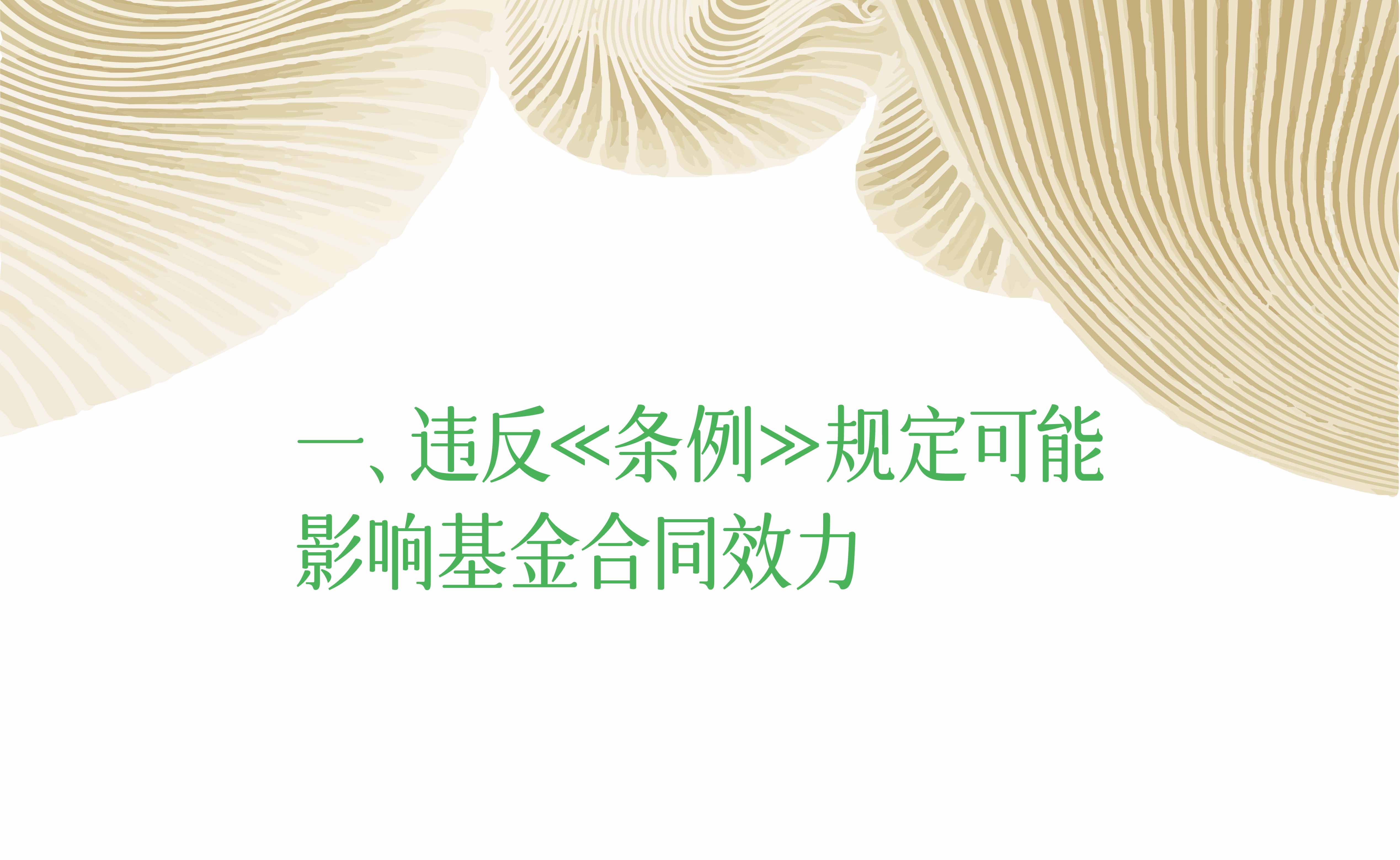
《条例》发布前,私募基金相关立法体系中效力层级最高的是《基金法》。但是,由于《基金法》大部分内容以公募基金为监管对象展开,关于私募基金的内容篇幅很小,且多为原则性规定。在私募基金实务中,规定更加细致、运用更多的是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以及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下称“《备案办法》”)《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等自律规则,但相关文件的效力层级较低。
《条例》在效力层级上属于行政法规,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可以援引《条例》的相关规定认定私募基金合同和相关法律行为的效力。但值得探究的是,《条例》中的哪些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过往司法实践中,法院以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否定私募基金合同或相关法律行为(如保底协议、补充协议等)效力的态度相对审慎,观点并不统一。例如:
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部分法院认为相关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1],未以此否定基金合同效力。
对于私募基金“保底协议”的效力,有法院以参照违反《基金法》关于禁止公募基金保底的规定认定私募基金的保底协议无效[2],也有法院认为相关规定不属于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
除上述易引发争议的条款外,也有法院认为《基金法》的其他条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北京金融法院认为,违反《基金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未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补充协议,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4]
我们认为,参照《九民纪要》第30条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界定[5],涉及金融安全、公序良俗的规定,例如禁止刚性兑付承诺、投资不得违反国家政策、不得要求地方政府承诺回购本金等规定,可能落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围。这一问题在实践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条例》将现有监管规定提升到行政法规的级别后,裁判机关如何具体认定和运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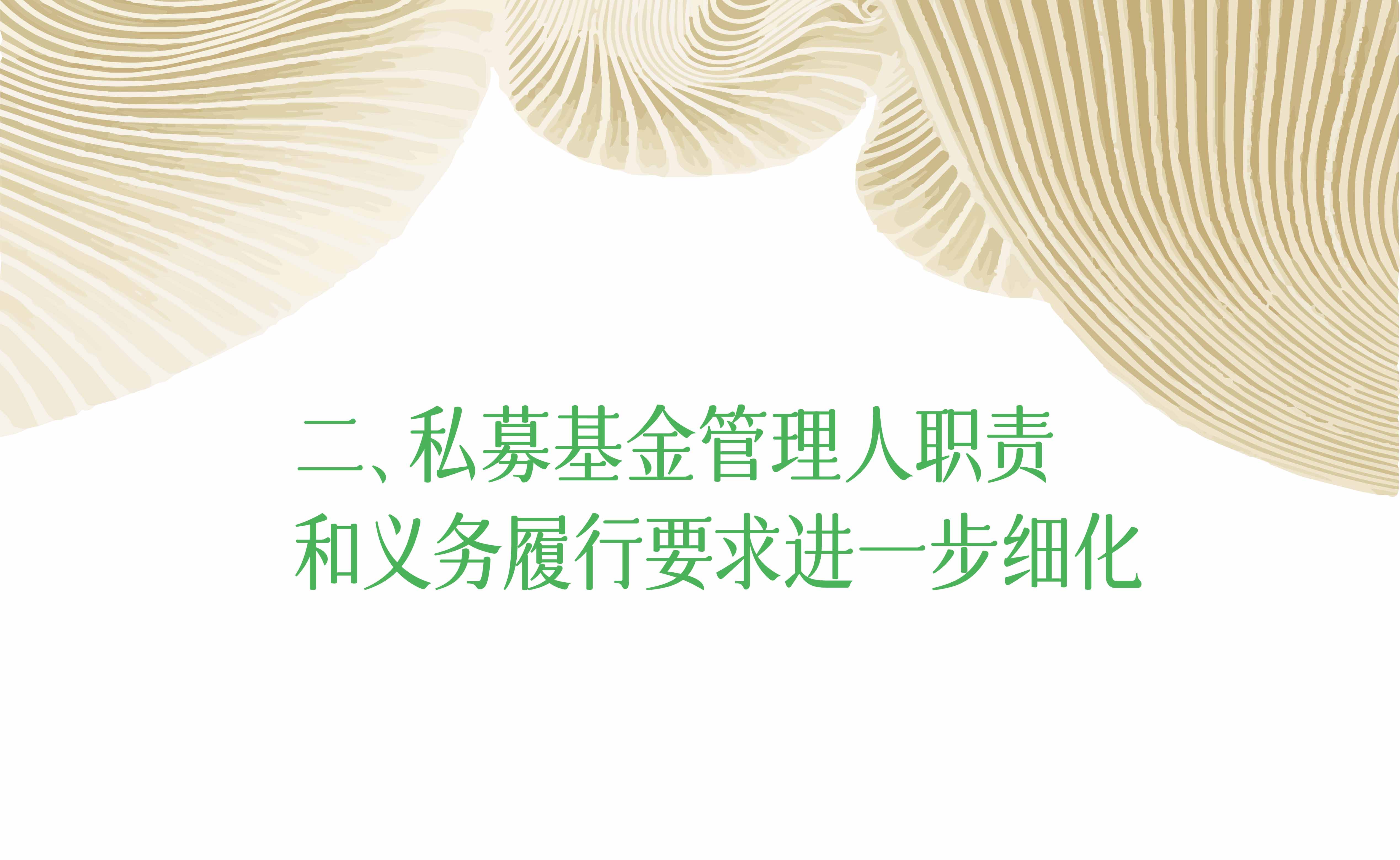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私募管理人应当自行募集资金,不得委托他人募集资金,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根据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匹配不同风险等级的私募基金产品。”
《条例》第十七条要求管理人原则上应自行募集资金,不得委托他人即通过代销机构募集,例外的,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规定与此前《暂行办法》《登记备案办法》《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6]有冲突,但与《登记备案办法》的规定[7]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理解,私募基金代销的窗口不会就此关闭,后续监管应当会制定出台相应的代销规则。但可以预见的是,不论是否允许代销,管理人适当性义务的履行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从展业的角度,募资能力较低的基金管理人展业将受到更多限制,这符合私募基金行业“扶优限劣”的监管精神;从争议解决的角度,上述规定对管理人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人主张管理人违反适当性义务有了更高位阶的行政法规依据。管理人需高度重视适当性义务的履行要求,按照相关规定建立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更加注重推介文件和合同文本合规性、做好募资人员培训及签约流程管理等,避免因此承担行政监管或民事赔偿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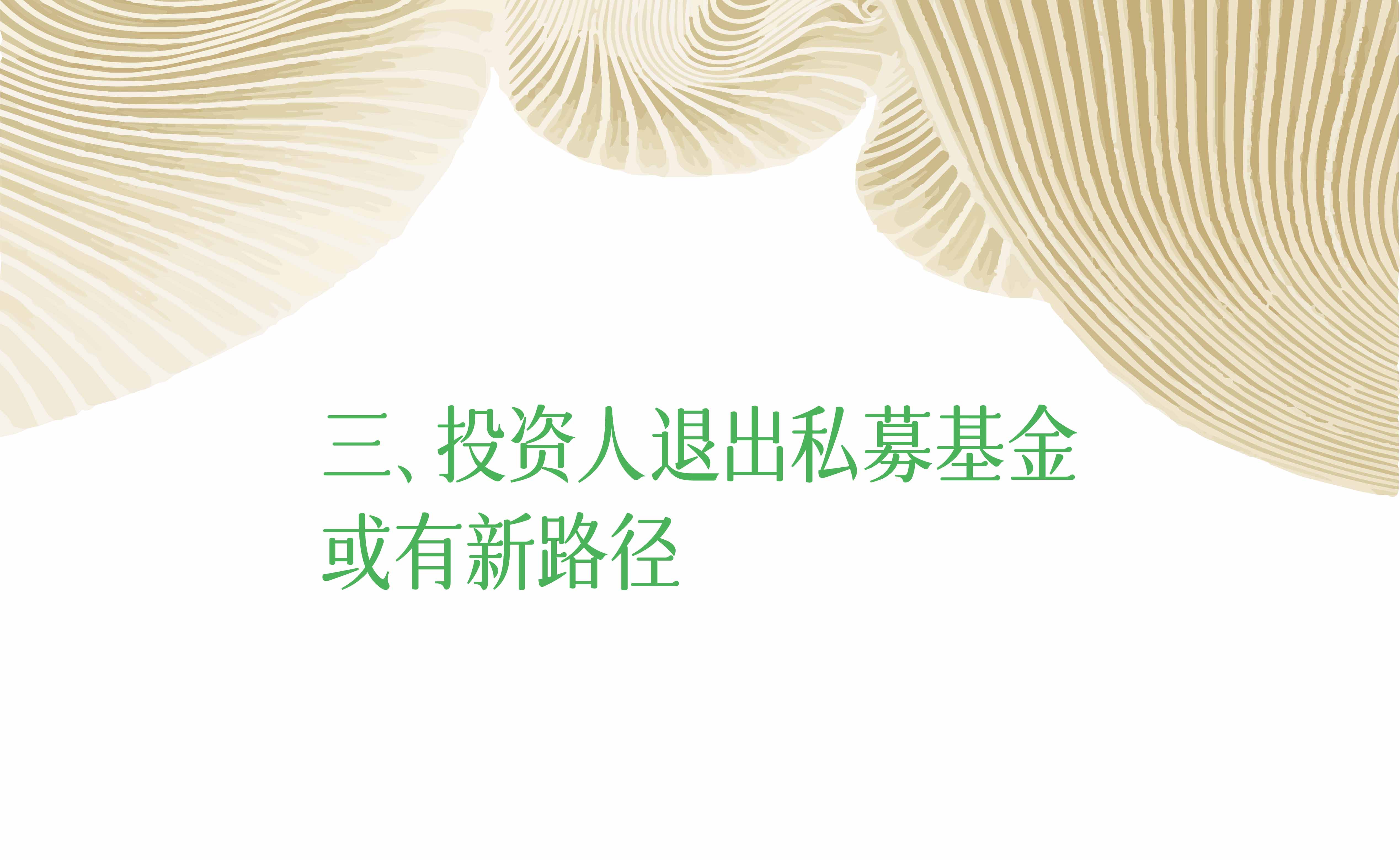
《条例》关于管理人履行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职责要求的条款主要如下:
1.勤勉义务
第十一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募集资金,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二)对所管理的不同私募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投资;
(三)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管理私募基金并进行投资,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
(四)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确定私募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五)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提供与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活动相关的信息;
(六)保存私募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
(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职责。
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为私募基金财产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2.忠实义务
第二十六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遵循专业化管理原则,聘用具有相应从业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投资管理、风险控制、合规等工作。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遵循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建立从业人员投资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第二十八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不得以私募基金财产与关联方进行不正当交易或者利益输送,不得通过多层嵌套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隐瞒。
私募基金管理人运用私募基金财产与自己、投资者、所管理的其他私募基金、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基金,或者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其他主体进行交易的,应当履行基金合同约定的决策程序,并及时向投资者和私募基金托管人提供相关信息。”
第三十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私募基金财产;
(二)利用私募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便利,为投资者以外的人牟取利益;
(三)侵占、挪用私募基金财产;
(四)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条例》的上述规定与现有监管规定没有明显区别,系统性总结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投、管、退”全流程的职责。在私募基金争议解决实务中,投资人和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已经习惯和熟练于援引和解释《基金法》《暂行办法》和基金业协会的相关自律规则,以论证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义务履行情况。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条例》增加了行政法规层面的明确依据,将证监会现有部门规章规定的职责纳入其中,也为后续证监会出台细化要求留下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为私募基金财产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在公司和合伙制形式的私募基金中,基金本身有诉讼主体地位,可以以基金的名义提起诉讼或采取相关措施。结合《条例》第二条“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或者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依法设立公司、合伙企业”的规定,我们理解上述“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讼权利”主要针对的是契约型基金的管理人,通过行政法规确认契约型基金管理人可代表基金提起诉讼/仲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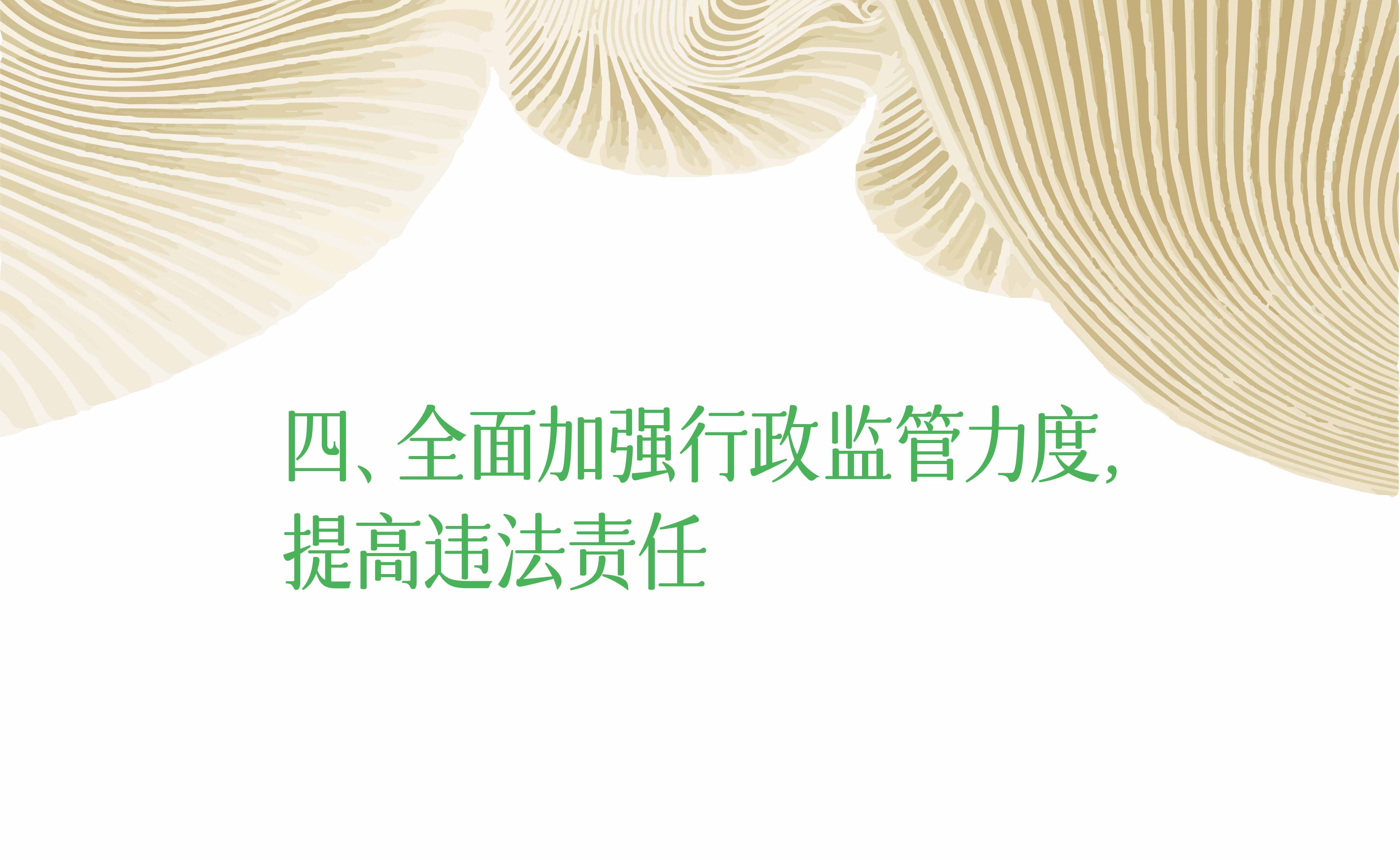
《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因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或者出现重大风险等情形,导致私募基金无法正常运作、终止的,由基金合同约定或者有关规定确定的其他专业机构,行使更换私募基金管理人、修改或者提前终止基金合同、组织私募基金清算等职权。”
上述条款的表述相对模糊和宽泛,为实践中如何理解和适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可能对投资人退出基金产生重大影响,为投资人退出提供了新的路径。
(一)“因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或者出现重大风险等情形”
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职的情形,例如管理人失联、被注销管理人资格、涉嫌刑事犯罪等,近年来层出不穷,《条例》的规定为破解该困境提供了出路。
根据《条例》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职不是触发该退出机制的唯一情形,在“出现重大风险等情形”时也可以启动。如何界定“重大风险”可能会产生争议,但投资人可以尝试与管理人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出现重大风险”的情形,以便该规定的实际落地。
(二)“由基金合同约定或者有关规定确定的其他专业机构”
第一,投资人与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中约定退出机制,例如指定管理人、托管人以外的其他专业机构,代表基金提起诉讼,负责基金的清算和收益分配,相关费用可由基金财产开支或可向管理人追偿。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基金投资人退出困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在合伙型私募基金中,管理人如怠于清算,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人往往难以基于《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启动合伙企业清算和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程序。《条例》的规定为投资人退出提供了新的制度工具。
第二,基金可以依据“有关规定”确定专业机构负责清算,这里的“有关规定”既可能包括后续相关机关发布的配套规定和实施细则,也可能包括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例如《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企业破产法》也规定了企业破产情况下破产管理人的选定。如参照上述法律规定确定专业机构负责清算,似乎也符合《条例》确定专业机构的“有关规定”依据。
第三,《条例》并未明确“专业机构”的含义,该表述十分宽泛,可以包括律师事务所,也可能包括破产管理人等专业机构。实践中,基金管理人可能因当前退出价格低、与交易对手协商其他退出方式等“合理”的理由,暂不采取诉讼仲裁等法律措施推进清算。也有管理人基于其他“非合理”的原因(例如配合其他基金退出、与交易对手达成其他安排等)拖延清算,致使私募基金投资长期无法退出。《条例》规定情形下第三方机构的介入,有助于控制前一种情形下管理人的操作风险,也可以避免后一种情形下管理人的道德风险,有利于投资人的退出。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过去十年私募基金行业快速发展,真假创新层出不穷,累积的风险也逐渐显现。私募基金争议多发,司法和监管实践中有诸多争议问题有待明确和解决。总体而言,《条例》是私募基金行业法规和政策的重要篇章,其内容基本延续了现有监管规定,但仍不乏亮点。在争议解决的角度来看,《条例》回应了过往私募基金展业和风险处置中暴露的部分问题,同时对部分疑难问题采取了搁置争议的态度。在监管与司法相向而行的大趋势下,《条例》对私募基金争议解决实务有重要意义。私募基金行业发展步入新阶段,《条例》对私募基金的争议解决与合规业务的影响和启示,值得进一步关注。
脚注:
[1] 杨漪清与汤涌、中投昆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1426号
[2] 赖文静、广州财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23878号
[3] 徐祖根与深圳市前海融信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金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其他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5民初64782号
[4] 杨丽丽与北京秃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2022)京74民终2035号
[5] 《九民纪要》第30条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6] 《私募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私募管理人委托销售机构销售私募基金的 ,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采取前款规定的评估、确认等措施。”《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托基金销售机构募集私募基金的,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基金销售协议,并将协议中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与基金销售机构权利义务划分以及其他涉及投资者利益的部分作为基金合同的附件。基金销售机构负责向投资者说明相关内容。”
[7] 《登记备案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自行募集资金,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委托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机构(以下简称基金销售机构)募集资金。”


